1418 阅读 2020-09-28 09:47:02 上传
以下文章来源于 汉语史与文献学微刊
转自“浙大汉语史研究中心”公众号
编者按:为了给年轻学者和在读博硕士生提供学习、研究汉语史的经验,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约请从事汉语史研究的十五位学者(出生于1970-1980年前后这一时间段)作了访谈,作为“汉语史研究系列访谈”的第一辑。本次访谈设置了十一个方面的问题,受访者可斟酌回答,不拘详略。在此衷心感谢各位参与访谈的学者对本次访谈的大力支持,同时也衷心感谢为访谈问题出谋划策的各位年轻朋友!
张定 副研究员
个人简介
张定,男,1977年生,安徽枞阳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汉语历史语法学、语言类型学和词典编纂。发表学术论文20篇,出版专著1部。参与《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的编纂和修订工作。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
1995年我从安庆市师范学校毕业后,先后在小学和中学任教,教学之余参加自学考试并于1997年获得汉语言文字学专业专科学历。1998年通过成人高考(专升本),考上安徽教育学院中文系,2000年获汉语言文字学专业本科学历。2000年考入徐州师范大学(现江苏师范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研究方向是现代汉语语法学,导师为张爱民教授。2003年至2007年,在安徽教育学院(2007年改建为合肥师范学院)中文系工作,讲授“语言学概论”“现代汉语”“古代汉语”等课程。2007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博士学位,研究方向是语法化和汉语历史语法学,导师为吴福祥教授。2010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事辞书编纂和科研工作。
我非科班出身,求学经历比较曲折,而且早期接受的专业基础训练以自学为途径,以考试为导向,因而知识结构并不系统,有先天不足。所幸后来进入专业领域的学习后,慢慢补了一些缺漏。硕士期间,各种语言学理论在汉语语法学界生根发芽并迅速本土化,语法化和语言类型学十分火热。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汉语拷贝式话题结构研究》(2003)在共时描写的基础上,通过历时演变和类型学的视角来观察现代汉语中的这一结构。历时研究和类型学视角都是为了解释现代汉语共时层面的系统和现象,这一研究和写作的模式已经成为我的信条。在高校任教期间,主要研究兴趣仍然是语法化和语言类型学,尝试写了《枞阳方言被动标记“着”的历史来源》(2006)和《汉语方言反复体标记的若干类型》(2007)。也曾不自量力,读了几本训诂学、音韵学、方言学著作和几篇相关论文,拼凑了一篇《枞阳方言本字考》(2004),至今仍不敢再看。读博期间,“语义图模型”由张敏、吴福祥等学者引入汉语学界。在吴福祥老师的指导下,我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图视角》(2010),论文以语义图模型为框架,借鉴语法化、语言类型学等理论,考察了汉语不定代词、情态词和“工具-伴随”介词三个语法专题。2010年以后,关注的领域有延续,也有变化。一是延续性的,比如《汉语的一种逆被动式》(2011)、《从“往”义动词到远指代词——上古汉语指示词“之”的来源》(2015)、《汉语否定不定代词的类型转变》(2019)。二是新拓展的,比如《“追逐”动词语义图》(2016)、《“穿戴”动词语义图》(2017)、《语文词典中疑问词非疑问用法的处理》(2015)、《“X差”类词语的句法语义问题》(2019),其中前两篇是尝试用语义图模型来处理实词的多义性,后两篇涉及语文辞书中某类词的处理。这几年“客串”词汇语义领域的直接原因是,十年来我的工作职责是语文辞书的编纂和修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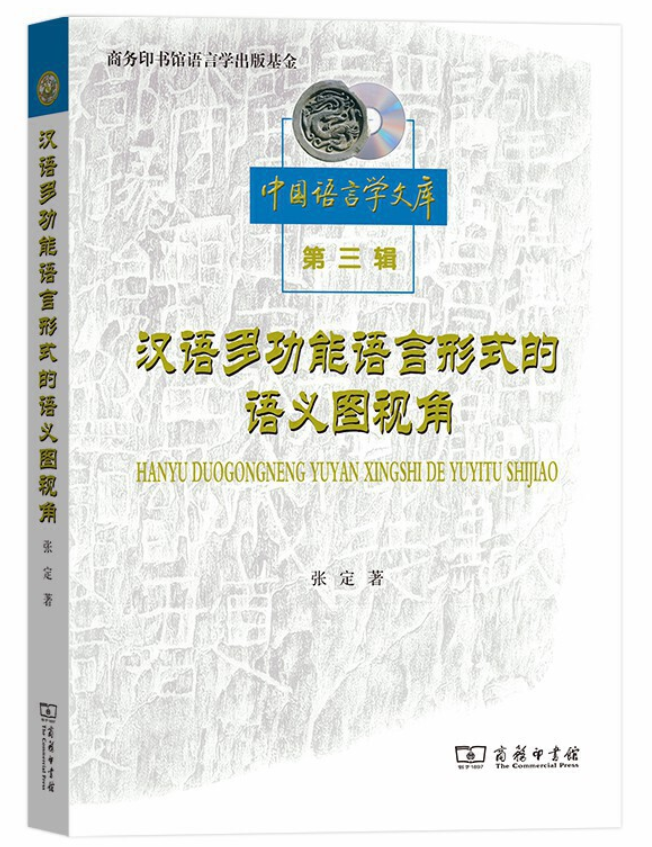
如前所述,目前的研究包括延续性的和新拓展的。如果有可能,我更愿意多做些延续性的研究。这些年积累了一些思考,但也在积压着。未来三五年打算把一些半成品和思考的内容整理一下,围绕两个专题展开。一是关于元语言、回声对语法语义演变的影响。读博期间,写了一篇关于枞阳方言回声否定词的文章,觉得“回声”这种现象挺有意思的。博士论文中也有类似的关注。后来就刻意去追踪这个问题,发现里面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因为这个问题涉及语言的自反性,可能会从根本上将影响语言演变的因素分为自反性和非自反性两类,尽管后者仍然是当前的主流认同。二是关于否定极性词的来源。这类词之所以成为一类,唯一的原因在于它们的句法环境,即出现在否定极性的语境。然而,从来源上看,这些词都有一些共同的语义基础,比如很多都表达了最小量、最大量或情态等。再长远一点,我想弥补一下知识结构的缺陷,多读些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的文献,积累一些古汉语词汇语义方面的知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想,可能还要写一部纯描写性的语法,要么是自己的母语,要么是普通话,要么是某一个断代文献或历时进程中的某个共时阶段。我觉得这是一个语法研究者的终极梦想或最终交代:你的所学所知所想终究要得到一个完备的共时系统的检验。
在您求学和研究过程中,对您成长影响较大的著作和学者有哪些(哪几位)?
学术是代代传承的,我们今天的知识结构主要源自三个方面:一是自己的导师、授课老师的课堂,二是同辈之间的影响,三是前贤的学术著作。
我的硕士导师张爱民教授,她给我最大的影响是她对吕叔湘和朱德熙两位先生的推崇。在她的课堂上,她大到方法论,小到无数的“最小对比对”(minimal pairs),不厌其烦地给我们分析句法结构。她特别重视朱德熙先生的《语法答问》《语法讲义》和吕叔湘先生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她能让你听完一个学期还觉得不够。她特别注重培养和训练语法本体分析能力,重视变换分析及其中的平行性原则。她还鼓励我们拓展视野,在结构之外寻求认知-功能上的解释。她带着我们出去开会,直面各自心目中的学术偶像,激发你对学术的热情和向往。硕士期间,廖序东先生以八十八岁高龄,为我们讲授《马氏文通》。他思路十分清晰,常能就某些细节问题详加展开。每次发给我们的讲义,都是他最新的手稿。先生人淡如菊,人格也堪称楷模。李申教授给我们开设了“近代汉语”课,主要研读一些近代汉语的文献,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到近代汉语的词汇和语法。从徐师大走出去的张谊生教授,常回到母校主持论文答辩。有一年他带回他在上海师大讲课用的语法化课程的讲义,我复印了一份,看了很多遍,这是我语法化的启蒙。张秀松教授是我硕士同年级的同门师弟,他抱负远大,刻苦钻研,立志要读遍当时学校图书馆的所有相关书籍。他真的这么去做了,而且很认真,很多英文的原著他读完后就留下了自己手写的中文版译稿。有一个这样的师弟,你不得不也去阅读,去做笔记。此刻我不可能不说起吴继光教授,尽管他未曾给我上过一节课,也未曾给我实质性的指导,但他是一面旗帜。可就在刚入学的那个学期,他离我们而去。多年来,他的灵光在我的脑海里一闪再闪,而不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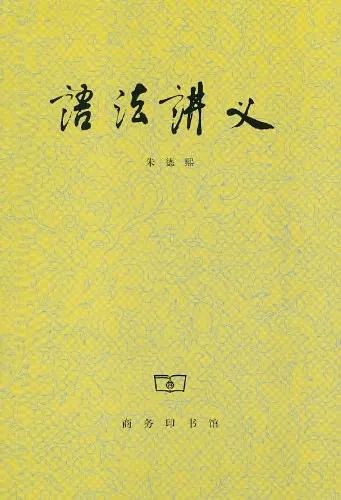


书影
在合肥任教期间,当时中文系主任张劲秋教授是我本科阶段的训诂学老师。他时时刻刻关心我的成长,无论是教学上,还是科研上,他总是不断督促我,及时提醒我。吴先文兄当时师从白兆麟先生攻训诂学,我们研究方向相对互补,彼此之间无所不谈,各自有所拓宽。
2007年,我考上了吴福祥教授的博士生,开始了迄今最努力、重塑人生的三年。老实说,之前我并不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但读博三年彻底改变了,几乎所有的精力都用来阅读、思考和写作,这无疑源自吴老师的示范和激励效应。吴老师在知识面上全面覆盖了我们,他以自己广泛的阅读,精选出语言学理论、历史语言学、语法化、句法学、语义学、语用学、语言接触等领域的若干经典著作,做成一份中西文书目,让我们慢慢去读。他将任何可能的场合都变成课堂,随时随地都在讲他的阅读和思考的问题,了解我们的学习进展。在毕业论文的选题上,吴老师让我关注当时正在引入汉语学界的语义图模型,这一课题也成为我关注最多的领域。总而言之,这种传统的师徒培养模式对学生学术的训练非常有用,甚至还能孕育超出师生之间的亲如家人的情感。读博期间,我很幸运在语言所学习了多门经典课程。方梅教授的“篇章语言学”引导我们从更大的篇章视角考察语法标记和话语结构,非常重视交际互动的语言观。胡建华教授的“形式句法学”提醒我们,句法语义研究必须落实在形式上。刘丹青教授的“语言类型学”将“漫山找矿”和“深井开挖”相结合,为我们观察汉语现象打开了一扇大门。张伯江教授的“功能语法导论”以若干代表性的专题为线索,几乎将几十年来汉语语法研究的历史融入其中。老师们渊博的学识和严谨的学风让我受益终生,我在写作中的很多想法都是直接来自老师们所授知识的启发。
多年来的阅读经历发现,有些著作对我的影响相对较大。硕士阶段,前面提到的朱德熙的《语法答问》《语法讲义》和吕叔湘的《汉语语法分析问题》等几部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经典著作,是我最初入门的底子。后来读了沈家煊的《不对称和标记论》,为书中简练的表述和论证的逻辑性所折服。刘丹青的《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袁毓林的《语言的认知研究和计算分析》,张伯江、方梅的《汉语功能语法研究》,张敏的《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等著作也开阔了我的眼界。考博时,为了系统地了解近代汉语语法的概貌和重要专题,我用心啃完了几本汉语历史语法方面的著作。尤其是蒋绍愚、曹广顺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史研究综述》和吴福祥的《语法化与汉语历史语法研究》,我将其中每一个章节中的重要内容和代表性的例句大段大段地摘录下来,A4纸密密麻麻地抄了一两百页,为了增强语感,我经常拿出来朗读,考试前差不多都能复述过来了。读博期间,Haspelmath的Indefinite Pronouns(《不定代词》)在语义图模型的操作上给了我直接的指引,也为我考察汉语疑问词非疑问用法提供了框架和理论来源。Croft的Typology and Universals(《语言类型学与普遍语法特征》)和Radical Contruction Grammar(《激进构式语法》)让人脱胎换骨,这两部书影响我的不是具体的分析操作,而是战略性学术思维的培养。此外,Traugott和Dasher的Ragularity in Semantic Change(《语义变化的规律性》),Bybee等的The Evolution of Grammar: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 the Languages of the World(《语法的演化:世界语言的时、体和情态》),Payne的Describing Morphosyntax(《描写形态句法》)等都是读后很有收获的经典之作。
发现并确定一个体量合适、有持续性的中长期研究对象,需要有充分的阅读准备。短线的操作,可能我们有了灵感,动手就写,几天就可成文,有时可能也不赖。但中长远的研究需要在广泛的阅读中淘沙,有了这个底子,就会清楚某个题目有没有意义,在学科领域处于什么样的层次,个人是否有能力去胜任,等等。
当前,博士论文可能是绝大部分学者进入学术门槛的通行证,也是同行评价其学术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凭据,其重要性自不待言。很多人的博士论文代表了一生的最高水平。目前我能看到的,若想在博士论文之外拓展前进,最重要的恐怕需要理论的加持和方法的更新,单靠研究对象的更换或许只能拓宽研究领域,无法提升研究层次。就博士论文以后的突破而言,后者更为重要。
对于汉语史研究而言,材料和理论都很重要,但硕博士研究生在有限的学习期限内对熟悉材料和掌握理论常常觉得顾此失彼,您对此有何建议?
我是带着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底子来研究句法语义演变的,加上先天不足,在汉语史材料上受过的训练较少,自身就是“顾此失彼”的典型。建议同学们去阅读其他学者的高见。有时,我们不妨换个角度想:如果我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材料导向的,或者我个人是以材料见长的,那么,我为什么一定要去寻找理论上的平衡?反过来也一样。在当前学科越来越精密化的时代,对于每一个在读的硕博士研究生来说,在有限的两三年,用“木桶效应”来要求或许过于苛求,能做好一端就已经不错了。当然,前提条件是都要达到合格,用起来不能出错。研究是一辈子的事,未来的路还很长,只要不放弃学术的追求,以后可以不断地调整。
对初涉汉语史学习和研究的硕博士研究生来说,您觉得哪些学术训练是必要的?在学术训练的过程中,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我的研究方向是汉语历史语法学。初涉这个领域,最好先去熟悉研究的对象,熟悉上古至近代汉语语法史的概貌,然后细读一些专题。有了这个底子,今后无论采用什么方法,都不至于跑偏。打算以语法描写为己任的,可以多关注描写对象本身,结合文献和词典,对所要描写的对象语言理解通透,将来写出的文章会很扎实。有志于理论解释的,可以选取自己认同的某一理论,精读这个理论流派的经典文献,将其一以贯之地用于所考察的对象,写出的文章可能较有新意。
在此过程中,有两点略作补充。一是语法分析。要学会掌握一种语法描写的方法,尤其要善于运用“最小对比对”揭示差异,发现规律。二是逻辑思维。研究要通过文章来检验,书面表达至关重要,而逻辑性又是重中之重。大到布局谋篇,小到例句安排,无不需要逻辑思维的支撑。我们在做出一个概括后,常常会发现例外,对例外如何处理、如何解释,决定了通篇内部是否自洽。
回顾求学和科研道路,您是不是也走过一些弯路?从中有无什么经验教训?是否可以结合具体经历分享一下?
有几件事对我的触动非常大。2013年,《汉语史学报》(第十三辑)赐版刊登了拙文《语义图模型与汉语几个情态词的语义演变》。这篇稿子是从博士论文中选取出来的,投稿时用的是简化字自动转换的繁体字,未仔细校对,文献征引体例也未做改动。后来,编辑部发来匿审专家意见,非常具体,令人无地自容。主要意见有:自动转换的繁体字要注意一些特别容易出错的字,比如“言说”义的“云”不能错为“雲”等;标明文献出处时,要采用规范统一的体例,有些信息不能放在书名号里。对于汉语史专业的研究者来说,这些甚至连最简单的常识性问题都够不上,而我居然在这些问题上出了错漏,无论是基础不牢,还是态度所致,都实在无法原谅。此事过后,我恶补了一点文献知识,在体例规范上更是细心严格,这对我后来从事辞书编纂和审稿校稿工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我想说的是,由于先天不足,有些入门之前的基本功我没做好准备,但一经提点,及时改正并严格要求,将会一生受益。
我曾写了篇文章,讨论汉语史上“及物动词+于(於)+直接宾语”的现象,认为这是一种“逆被动式”(antipassive)。后来,我的师妹王丽玲也讨论了这一现象,并称之为“降宾式”(object demotion)。拙文称之为“逆被动式”的主要依据是直接宾语以旁格(oblique)的形式出现,功能上也非常符合。但Payne(1997)提到,逆被动式和降宾式最重要的区别是,逆被动式中动词带有某种专门的逆被动化标记或不及物标记,而降宾式则没有这样的标记。我当时想,汉语并非形态型的语言,如果还要以是否带不及物标记为标准,那我们也可以说,汉语也没有真正的被动式。何况,Payne(1997)也提到,Heath(1976)便将降宾式当作逆被动化的类型。这里我想表达的是,面对同一种语言现象,你是往前进一步,贴上某个标签,还是老老实实采取一种相对稳妥的中立的做法。放到现在,我一定会退一步,称之为降宾式。
您是如何平衡自己的科研和日常生活的?如何看待网络上传说的高校青年教师“007”(零点上班,零点休息,一周工作七天)的生活模式?您平常都会怎么放松身心呢?
需要平衡的体现在方方面面。博士毕业后,本职工作是辞书编纂和修订,这项工作是需要长期耕耘的细活儿,要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校对,常常手头上同时有几部辞书的活儿。多年下来,责任心和耐心都得到了锻炼,积累了一些素材,学术的路子也拓宽了。科研有所耽搁,但理想未曾泯灭。学术思考从未间断,每年会参加几次学术会议,只是下笔落实十分缓慢,有一次整理材料,发现积压了不少未曾完稿的PPT,心下自责不已。在这两件事的平衡上,基本原则是:本职工作第一,有任务按时完成;有余力就落实写文章。于是我总是觉得没有什么余力。另外,这两项工作给人带来的体验是不同的。编字典过程繁琐甚至枯燥,但结果能带来愉悦:那么多人在使用《新华字典》和《现代汉语词典》,偏偏你就这么幸运地参与其中;写文章的过程于我总是满怀愉悦,我从来没有痛苦地面对写作,但结果常常不能尽如人意:在你的心里,那些传世的经典之作时刻高悬在上,闪闪发光。
我没有本科生的教学任务,近来开了两门研究生课程。教学内容自己相对熟悉,专门投入教学的时间并不多,加上学生素质很好,教学相长。我还要直面的现实是:主持家务,几近包揽;膝下二犬,年幼待哺。我很喜欢做这些事。当你洗晒叠放家人的衣服,当你擦拭整理每一张桌椅,当你做好饭菜端上桌来,当你看到二犬争食,一天天长大,你会毫不犹豫地确定,你是在做最正确的事情,而且过程和结果都让人愉悦。
每天晚饭前去公园跑步,一圈下来,六七千米,足以大汗淋漓。喜名家翰墨,尤爱二王、颜真卿、米芾、董其昌,常捧帖赏读,意犹未尽时,取笔对临,眼里心里,纯然只有黑白,无比清净。或与师友三五人,相约餐叙,谈笑风生,所有的累都消散了。
往期回顾
下期预告
“汉语史研究系列访谈”(第一辑):田炜教授
相关工具













